
图书
 登录
注册
登录
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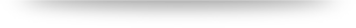
- 内容简介
- 书籍目录
该书从彝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中发掘太阳历的文化意义,认为天文历法之太阳历为我们打开了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由此窥见中国文化中道、阴阳、五行、四时、八节、十月、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年、岁、气等范畴概念编织成的中国文化图景的奥秘。
The book explor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olar calendar from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i, Miao, and Shui ethnic minorities, and argues that the solar calendar of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opens the door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us glimpses the myste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landscape woven by the concepts of the Tao,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four seasons, the eight festivals, the months of October and December, the twenty-four seasons, and the categories of the year, the year and the qi in the Chinese culture.
-
唐诗镜像中的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in the mirror image of Tang Poetry -
中国逻辑史研究.第一辑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First Series -
中国与拉丁美洲留学人员交流与培养:回顾、现状与展望
Exchanges and Cultiv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Review,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
中国礼学思想发展史研究:从中古到近世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ITE THOUGHTS:From Medieval to Early Modern Times -
清代文官行政处分程序研究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Procedures of Civil Officials in Qing Dynasty
